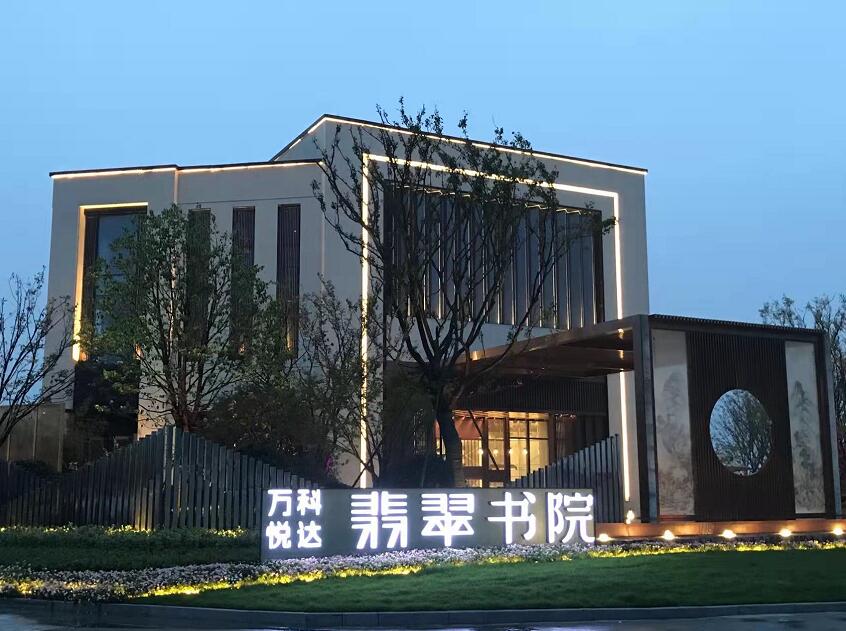它们可能�5严实实。
它们可能贴在树上、房檐,甚至你家大门上。泛滥时,过街天桥的阶梯上,一脚下去是重叠四五层的小广告。还有胆大的,在警车、城管车,还有康熙年间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广告的印记。
习惯了基地里整齐的红砖楼房,裴延印夫妇接受不了“乱糟糟”的北京。接受了30多年的军事化管理,做卫生早已成为习惯。老两口决定用小铲对抗这些小广告,也算是打发退休生活。
早晨6点到9点,下午4点到7点。几乎是固定的时间,他们会牵起小狗“毛毛”出现在家附近的街头巷尾。时间久了,“毛毛”有时候看见地上的小广告也会用爪子扒拉。
这些年,小广告的黏性越来越大,贴得也越来越高。裴延印把裁纸刀片缠上硬纸板,再用透明胶捆好。刀片经常刮坏,家里就放十多把备着。他还把可伸缩的拖把杆卸了,改装成1.5m的长铲。
最难弄的是贴在地上的小广告。人的重量加上胶水的粘合,来回踩过千百次后,薄薄的一张纸就像是和地面长在了一起。有一次,裴延印把指甲抠劈了,血肉模糊。一年后,灰突突的新指甲顶出皮肤,从此他揭小广告时总会戴上手套。
想尽办法的不止他们,面对着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满伤疤的铁器,环卫和城管用上了高压水枪、高端树脂雾化专业城市清洁机、能把钢铁打得锃亮的水砂枪,以及专门为胡同小巷设计的小三轮蒸汽清洗车……
2007年,北京曾推出《各类市政设施防护性涂刷规范(试行)》,规定3米以下的市政设施均应粉刷防护性涂料。电线杆、牌匾、雕塑等钢结构表面有了“保护膜”,一口气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广告。但是,这个规范难以落地——公共设施数量大、涂料费用高。
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统计,1张小广告的成本不到0.1元,但清理成本却达0.68元。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里每年就要花费约1.36万元,仅西城区一年投入就要1300万元。
面对小广告,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是束手无策的。它们铺天盖地,今天铲了,明天就像野草一样又重新出现。在清理和粘贴的反复拉锯中,最后受伤的是那些公共设施——小广告与金属防腐漆一起脱落,逐渐生出红褐色铁锈;为盖住印章小广告刷下的白漆,像极了一块又一块补丁。
社会管理学者王力一直关注小广告治理问题,曾出版《一指缠——“老剪报”杠上小广告》一书,他将小广告泛滥的原因归结于“需求”。改革开放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,以前开锁、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,后来都可以花钱雇人做。社会化分工解决了生活中部分难题,也带来了城市病。登不起广告的人,想出小广告的方法来增加客源。“破窗效应”之下,众人皆效仿。
但低成本也成了违规、甚至违法行为的温床,那些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,通向的不仅仅是生活服务,也可能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
当时的惩处力度并不小。2002年,适用新的《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,东城区城管大队捣毁一个散发百万张小广告的公司,一次性开出一万元的罚单。2014年,北京警方启动打击整治非法小广告专项行动,并在30天内共查获非法小广告违法人员4000余人,收缴非法小广告41.2万余张。2016年,北京向组织散发小广告的房地产企业开出40万元罚单,创了北京城管执法部门针对非法小广告罚款的最高纪录。
可是张贴小广告带来的收益也很大。张贴小广告的日薪从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,一些不懂事的学生,把它当为勤工俭学。2006年时,有人靠贴小广告收入超过10万元。那一年,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万元。
合力
对于裴延印来说,在漫长的28年里很多时间点已经模糊了,但是2008年一定是个节点。那一年,北京举办奥运会。世界的注视,使得治理“城市牛皮癣”这件“小事”变得要紧起来。
也是那几年,在各个区、街道、社区的宣传下,手拿小铲的形象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老人世界里的一股“潮流”。
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区,居民们用小铲刀对抗牛皮癣,有人把装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来,攒一堆儿,拿水稀释成糊糊,往墙上一刷。等干透了,小广告就能翘起来。
在天安门地区城管局工作过的资深队员韩东(化名)回忆说,小广告最泛滥的那几年,他负责的区域每个路口都有十多个小广告发放者,他们站成一排往游客手里硬塞,环卫工人前脚扫了,后脚游客又扔了。就别提贴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,光是收集过往游客手中的小广告,一米多高的大袋子,一天就能装四五袋。
“北京是全国的门脸,他们这就是往脸的鼻子尖儿上贴。”韩东说,那时,天安门地区城管局的工作里,清理小广告的任务占到了60%。
在这场长期的猫鼠游戏中,双方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他们既是陌生人,也是“熟人”。
和小广告打交道多了,韩东甚至一眼能看出哪个号码经常出现。有时正碰上他们散发,韩东支起伞遮住脸,大步走过去,一抓一个准。有的人向他求饶,第二天又被逮到。久而久之,贴小广告的人看走路姿势都能认出他来,狂奔到100米外还扭头冲他笑。
有一段时间,裴延印和贴小广告的人达成一种奇怪的“默契”——每天下午4点,有几个年轻人会在立交桥下等他,等监督的人走了,桥下树坑里多了个垃圾袋,里面密密麻麻都是没贴的小广告。
在裴延印眼里,贴这些小广告的年轻人几乎是他儿孙辈的孩子,他尽量不与他们争执,只希望教育两句,引他们走向正路。
韩东也有很多无奈。很多小广告散发者都是些游手好闲的“小年轻”,从全国各地漂到了北京,晚上住桥洞,在公厕洗澡,白天就出来发传单、贴小广告。韩东查处过年龄最小的小广告散发者只有6岁。
年轻的队员经常被他们问蒙,“发小广告违法吗?我没钱挣,得吃饭啊!”
小广告与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,使得本就一团乱麻的治理难上加难。
战斗
清理小广告和贴小广告的斗争,大部分时候像是在游击战,有时也会正面遭遇。
裴延印记得,2012年的一段时间,他一连几天都看到,自己前一天铲掉的地方,第二天又贴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小广告。后来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个小时,看到年轻人娴熟地将胶水挤到小广告背面,“啪”一下摁到了电线杆上。
年轻人贴一张,他就撕一张。
“你是不是没有钱吃饭了?揭广告多少钱一斤?”年轻人质问道。
“我不缺这点钱。别人往你脸上贴一块破纸,你愿意吗?”老爷子教育他。
年轻人不听这一套,威胁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广告,就把他的小狗摔死。争执之下,他向裴延印挥了一拳。裴延印闪了过去,眼看冲突就要升级,附近巡逻的城管队员赶来,年轻人才寻机溜走。
裴延印是幸运的。这样的威胁恐吓在那个时期并不少。有人恼羞成怒,在小广告上诅咒“老太太撕一张少活一天”,有人冲着16岁的医院保安刺5刀,刀伤离心脏只有几厘米。
直至2013年,一名57岁环卫工因清理小广告被殴打致头部缝针,再次引发众怒。
如今,“城市牛皮癣”已经就要成为一个被写进历史的词语。与小广告张贴者斗智斗勇的日子逐渐远去。金大钧围着社区里286棵老槐树转,看不到一张乱贴的小广告。 但裴延印还没有停下来,他要继续追击“穷寇”。9月25日上午9点,他和老伴何秋兰提着买来的蔬菜和铲下的“战利品”溜达回家。小区周围零散的小广告早已被他们清除一空。 时间走过28年,坚持下来的动力不只是闲来无事的排遣,更像是一种“瘾”。回味起那些与贴小广告者较劲的日子,成就感不仅来自城市变干净了,也来自一次次收获战利品时的满足。 没有人统计过他们俩铲除的小广告,但是少说也有几百万张。不光自己撕,他们还带动着221厂以前的老同事们一起撕。 工作过半辈子的基地住进了藏族同胞,他们邀请裴延印与何秋兰回去看看,老两口推脱了好几次——他们是社区里五六个志愿组织的骨干力量,没空出去玩。 记者 郭懿萌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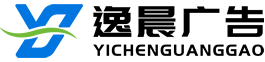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